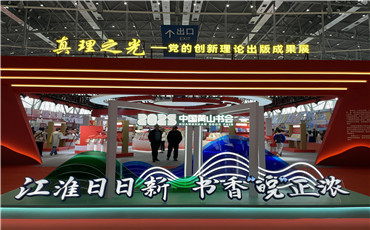7月25日,合肥市包河區藍藻科普館外,技術人員利用混凝-氣浮工藝從藻水中回收藻泥。
我的名字叫藍藻,是一種最原始、最古老的藻類生物。在夏日驕陽曝曬下,巢湖里的我會肆意生長,浮在水面產生異味。為了讓巢湖變得更加美麗,近年來,人們通過打撈、深井控藻等各種方法治理我產生的“生態難題”,我們的水華面積不斷縮小,沿湖也沒了明顯異味。但我并非一無是處,為了讓打撈上來的我們發揮更大的利用價值,今年以來,來自合肥工業大學的科研團隊對我進行生物質資源化的轉化工藝研究,我的“變身之旅”也就此開啟。

7月28日,合肥工業大學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生物質資源化轉化團隊負責人馬曉靜在培養箱里觀察不同藻類品種的生長情況。
聽說吸藻口能靈活調節高度,專門捕捉最密集的藻群,在合肥市包河區的藍藻科普館周圍,我和同伴們被吸藻管道送進了微納米一體化除藻的中試設備里,在通過了安徽省科技成果鑒定的生物絮凝劑BGA的作用下,我很快便浮到了水面上并被刮板刮進收集槽,通過疊螺機像揉面團似的被擠壓出水分,這時候的我變成了含水率90%的藻泥。而真正的“蛻變”是在藍藻水華微波脫毒脫水設備里發生的,我被送上傳送帶,微波能量穿透了身體,僅僅20分鐘我身上的水分就降到10%以下,微波悄悄破壞了“臭名昭彰”的藻毒素,我也被烤成了類似于“海苔”的塊狀薄片。

7月25日,合肥市包河區藍藻科普館外,技術人員將微波干燥后的“藻苔”裝瓶取樣。
變成薄片的我被帶到合肥工業大學食品與生物工程學院的實驗室里,在這里,我遇到了許多的新朋友——小球藻、柵藻等,科研人員對我們進行了營養評估與組分分析,生物質資源化轉化團隊負責人馬曉靜在實驗中發現,與綠藻家族相比,通過干燥處理后的我不僅蛋白質含量豐富,而且氨基酸組成與魚粉、豆粕、菜粕相比具有一定優勢,我竟然有潛力成為高營養價值水產飼料的添加原料。于是,馬老師帶領團隊通過產學研合作的形式簽訂技術開發合同,推動研究成果的工程化應用。

圖中樣本從左到右依次是藍藻藻水—藻泥—分離后的水—干燥后的“藻苔”。
嗡嗡嗡……伴隨著粉碎機的吵鬧聲,我被磨成了綠色的藻粉,經過和豆粕、面粉等按比例混合后,通過制粒機制成顆粒狀的魚飼料。下一步,我便要去參與小規模的水產養殖試驗,收集魚蝦對我的評價和反饋。科研人員說,每10噸藻泥就能制成1噸藻粉,替代0.9噸的魚粉。


7月29日,國家級安徽巢湖斑點叉尾鮰良種場內,工作人員使用藻類飼料開展水產養殖試驗。
從困擾水體的“綠潮”到水產養殖的“營養餐”,這場變身不僅讓巢湖的水更清,也讓我找到了另一種存在的價值,懂得了變廢為寶的智慧。我也期待著,自己能早日在水產養殖領域大規模應用推廣,真正實現從湖中來回到湖中去。

7月25日,巢湖北岸,安徽清耀環保工程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員利用水槍沖散聚集的藍藻。
記者 程兆 攝影報道